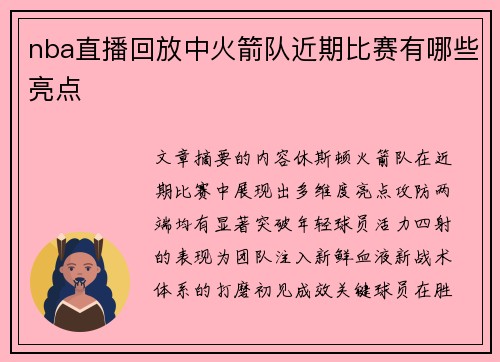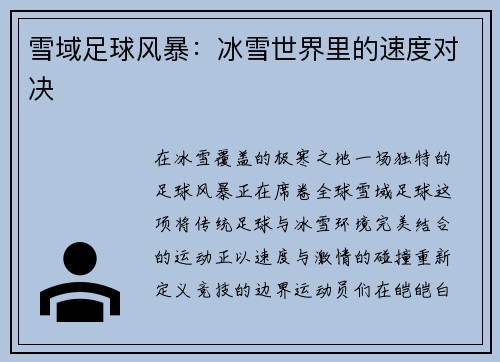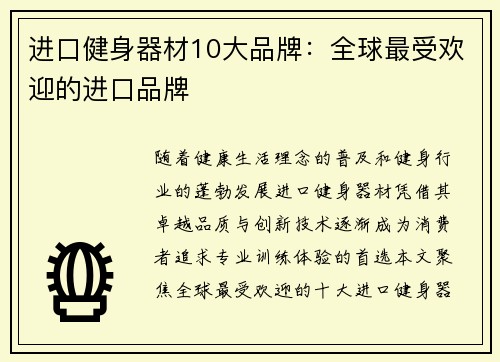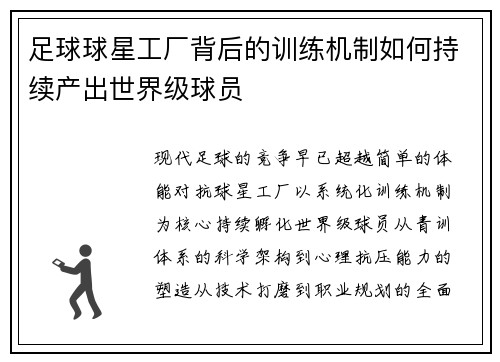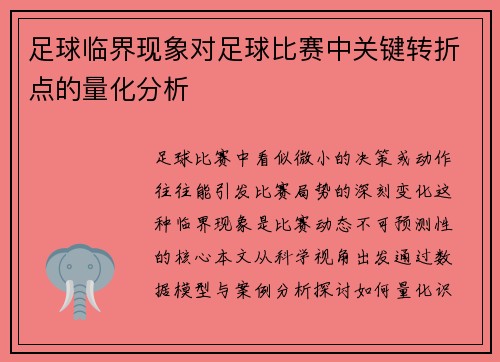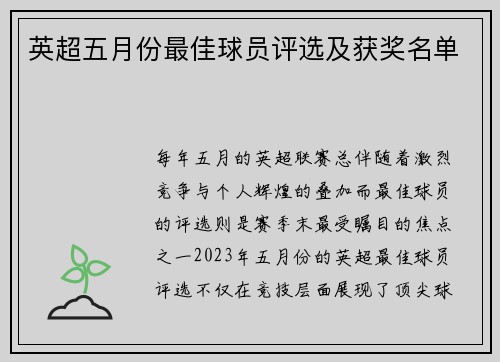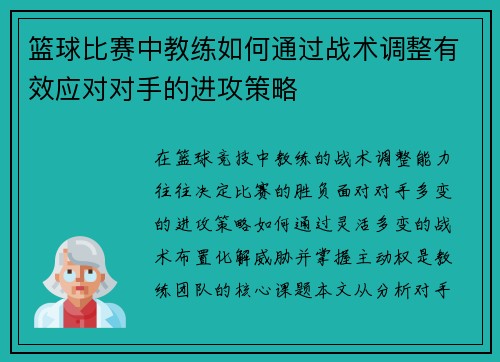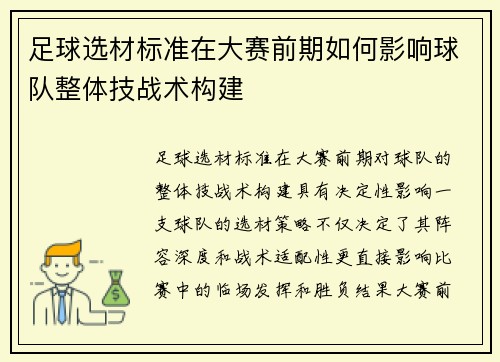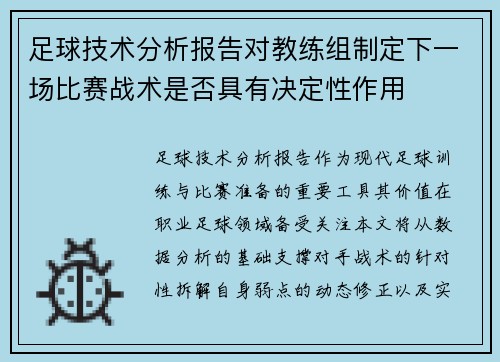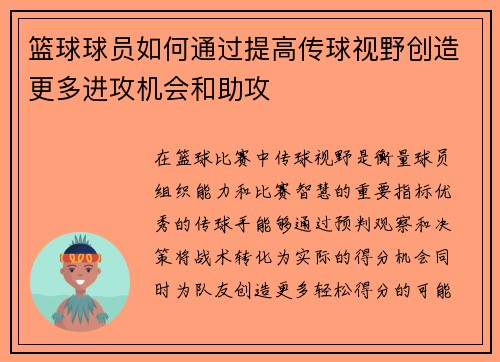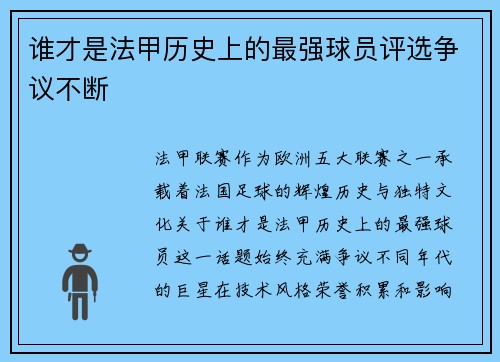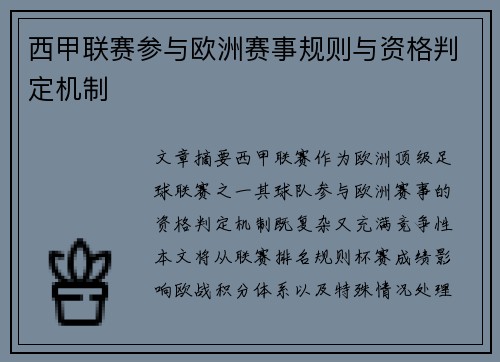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自成立以来,其球队的归属变迁与主权演变始终是职业体育发展的重要课题。本文通过梳理CBA球队产权结构的四次重大变革,分析资本力量对俱乐部控制权的渗透路径,探讨法律框架下球队主权的界定难题,并展望职业体育产权改革方向。球队名称更迭背后折射出职业联赛商业化进程中的利益博弈,地方体育局与企业集团的权责划分直接影响着联赛生态,而球迷文化认同危机则暴露出职业体育发展中的深层矛盾。
职业篮球产权结构演变
CBA初创阶段实行地方体育局主导模式,各省市专业队直接改制为职业俱乐部。这种体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体工队管理特征,球队产权归属于地方体育行政部门,教练团队与球员人事关系仍属事业单位编制。此时的职业化改革更多停留在赛事包装层面,实质运营仍由政府专项拨款支撑。
2005年准入制改革推动产权结构首次裂变,民营企业开始通过注资方式获得俱乐部部分股权。深圳马可波罗、浙江广厦等球队开创公私合营新模式,企业获得商业开发权而体育局保留人事管理权。这种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产生决策权分散问题,重大引援需双方协商,常因理念差异导致效率损耗。
2017年管办分离政策实施后,完全职业化俱乐部数量突破半数。新疆广汇、北京控股等企业通过整体收购获得完全控制权,形成市场化运营体系。但急速商业化引发新矛盾,山西汾酒集团撤资导致球队濒临解散的案例,暴露出资本短期逐利性与球队长期发展的冲突。
资本渗透与主权博弈
房地产企业的深度介入重塑了联赛资本版图,超过60%俱乐部现由地产集团控股。这些企业将球队作为城市名片进行品牌营销,广州龙狮迁址佛山更名事件,反映出资本方对球队地域属性的工具化利用。巨额投资虽提升竞技水平,却削弱了球队与原生地域的文化纽带。
互联网资本入局带来全新运营思维,哔哩哔哩收购上海大鲨鱼开创二次元营销模式。新媒体平台通过赛事版权分销重构盈利模式,但也引发球队主权让渡争议。腾讯体育与吉林东北虎签订的数据独家协议,实质上架空了俱乐部的商业自主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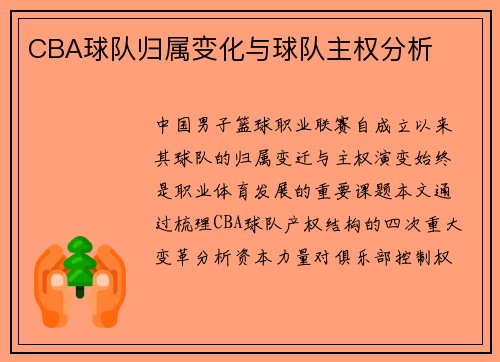
外资参股引发的主权争议在南京同曦案例中尤为突出。韩国三星集团试图通过技术入股获取决策席位,遭到中国篮协的严格限制。这种主权捍卫既保护了联赛自主性,也暴露出职业体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壁垒。
法律框架与权责界定
现行《体育法》对职业俱乐部产权归属缺乏明确定义,导致江苏肯帝亚股权纠纷案陷入法律真空。球队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缺失,使得赞助商权益与投资者产权边界模糊。上海东方俱乐部商标权争夺战历时三年,最终依靠行业协会调解而非司法裁决。
劳动合同制度改革滞后于产权变革,体制内球员的"双重身份"引发转会纠纷。山东黄金时期遗留的事业编制球员,在球队被西王集团收购后出现社保衔接障碍。这种人事制度与产权结构的不匹配,制约着球员市场的流动性。
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均衡分配加剧了地区竞争失衡。东莞银行享受的地方财政补贴是山西俱乐部的五倍,这种政策性倾斜导致中小城市球队难以维持运营。主权归属差异带来的资源获取能力差距,正在扭曲联赛竞争生态。
文化认同与发展困局
频繁的球队迁徙严重消耗球迷情感积累,重庆翱龙北迁北京更名北控,导致原有球迷基础流失率达78%。地域文化符号的随意变更,使得深圳烈豹这样的老牌球队面临身份认同危机。年轻球迷更倾向于追捧球星而非俱乐部,折射出文化根基的脆弱性。
青训体系与产权结构的脱节制约长期发展,广东宏远模式证明自有产权与青训基地的结合最具可持续性。但多数俱乐部依赖短期买人策略,浙江稠州银行十年间青训投入仅占总预算12%。这种急功近利的运营方式,削弱了球队主权延续的人才基础。
联赛品牌价值过度依赖顶级球队,辽宁、广东等强队贡献了70%的媒体关注度。中小球队在转播分成体系中的弱势地位,迫使其不断寻求资本并购。这种马太效应正在形成"主权强者恒强"的恶性循环,威胁联赛整体竞争力。
南宫体育总结:
CBA球队的归属变迁史实质是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缩影,产权结构的每次调整都牵动着多方利益平衡。从行政主导到资本驱动,主权转移带来的不仅是运营模式革新,更是职业体育本质属性的回归探索。当下俱乐部在市场化与公益性之间的摇摆,暴露出职业体育立法滞后与制度供给不足的深层矛盾。
未来改革需建立产权流转的规范体系,完善无形资产评估机制,构建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的弹性边界。在保障投资者权益的同时,应确立球迷文化权益的法律地位,探索社区持股等新型治理模式。唯有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动态平衡,中国职业篮球才能真正完成从商业赛事到文化载体的质变。